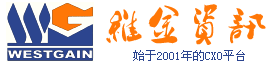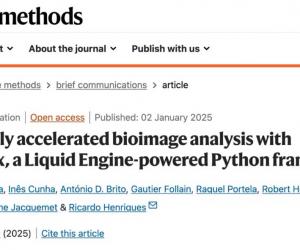扎克伯格“读书年”再次荐书:《理性的仪式》
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读书年”中推荐的第7本书是来自崔时英(Michael Suk-Young Chwe)的《理性的仪式》(Rational Ritual)。在这里,我们总结了5个关键的概念(以及一些背景简介)。扎克伯格希望,这些概念将协助定义Facebook社交媒体帝国的未来。
我们很多人都会观看“超级碗”比赛,并为其中展现的运动技巧和运动能力而沉醉。而对广告而言,它们将可以覆盖同样多的观众。许多广告主都会争夺“超级碗”比赛期间的广告播放时间。用崔时英的话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能极大地提升销量和客流。
扎克伯格“读书年”挑选的第7本书,即崔时英的《理性的仪式》,从博弈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君主制、制度变革、宗教和仪式演讲。根据博弈论,某项活动的结果取决于参与活动各方做出的选择。随后,这本书还探讨了“合作问题”,人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为何我们的决策几乎完全基于社会群体的做法。

内容简介
在《理性的仪式》一书中,崔时英并不仅仅对“超级碗”进行了分析。他还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仪式、典礼和媒体事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很多年中,这些仪式被用于形成“常识”,帮助人们解决问题,例如需要遵守哪些规定,可以购买哪些产品。这本书对于了解罗伯斯庇尔和史蒂夫·乔布斯等人的行事方式很有帮助。
扎克伯格挑选《理性的仪式》一书是为了深入了解“常识”的概念。在Facebook发展至今天的过程中,这可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扎克伯格表示,常识“是设计社交媒体时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需要在创造个性化体验和开发通用体验之间进行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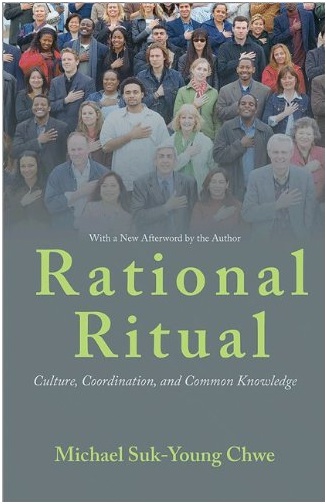
Rational Ritual
作者简介
崔时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主讲博弈论。他同时也是《简·奥斯汀,博弈学专家》一书的作者。
书中的3大重点:
1.合作问题常常通过“常识”得到解决
假设你是一名艺术记者,获得了参加某一画廊开幕的邀请。两天前,你听说,由于画廊中展示的作品存在虐待动物的内容,画廊本身遭到了抗议,那么你是否仍要参加此次开幕活动?你的决定可能取决于是否会有其他记者前去那里。这就带来了合作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人参加,那么所有人的参加意愿都会提升。
那么,这一问题要如何解决?崔时英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其他所有人是否接受邀请,而其他每个人也必须知道另外所有人的情况。因此,邀请本身必须是一种常识,就像是群发电子邮件中的内容。如果常识告诉你,你不会是前往那里的唯一一名记者,那么你很可能就会前去。
2.常识往往通过仪式来形成
常识是解决合作问题的关键。因此,权力的所有者,包括政客和宗教人士,会通过仪式来强化他们的权力。例如,皇家巡游就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国王会逐个城市地视察自己的领土。
这一过程中,许多农民会聚集在巡游路线上,目睹国王的统治力。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农民将会看到其他人,并知道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国王的权威。
3.你的好友可能无法帮你找到工作,但熟人或许可以
在《理性的仪式》一书中,崔时英表示,熟人之间迅速发展、有形的弱关系更适于沟通。而密友之间逐渐形成的强关系更适于合作。弱关系网络,或者说熟人网络能够更快地发展,给你带来更多联系人。
实际上,如果将熟人的熟人计算在内,那么你会发现已经拥有了庞大的人际网络。弱关系网络的广度意味着沟通,例如对工作机会的介绍,将会比强关系网络更快。许多知识将会更快、更广地传播。
书中谈到的一个有趣事实
崔时英解释,即使你否认这一观点,但如果有很多人购买某一商品,那么你购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这适用于许多“社交”商品,例如啤酒、服装和电影。对于这些商品,人们更倾向于流行品牌。因此,对这类商品的广告实际上是常识形成的过程。广告主不仅希望你看到广告,还希望你知道,有许多其他人也看到了广告。
电视广告的数据显示,相对于非社交商品,社交商品的广告主通常需要支付更高的千次展示成本,同时能覆盖更多的广告受众。因为他们的广告通常需要在热门电视节目(或是“超级碗”等大型活动)中播出。广告主选择这样的节目和活动是由于,它们更有利于形成常识:所有人都知道,有很多人在观看这些广告。
书中谈到的一个古怪事实
18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曾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这可能将会是权力的终极形态。
在圆形监狱中,囚室围绕着中央的看守“大厅”来排列,这将防止所有人的沟通、合作,以及常识的形成。在圆形监狱中,可见性是中心化的,即看守可以从中央大厅看到所有囚徒的情况,但囚徒之间无法相互看到对方。
从理论上来说,圆形监狱的设计不仅导致囚徒不再掌握任何权力,也能使成本降低。因为囚徒永远不会知道,他们何时在被监控。他们需要假设自己处在持续被监控的状态中。因此,他们将会自我监督。
最重要的一点
为了解决合作问题,我们需要常识:我们知道信息,并且知道他人也知道这些信息。这种常识的形成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行为、仪式,以及“超级碗”等媒体事件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