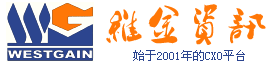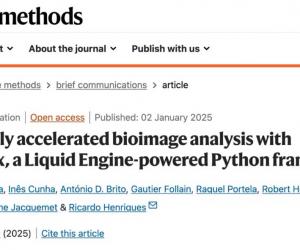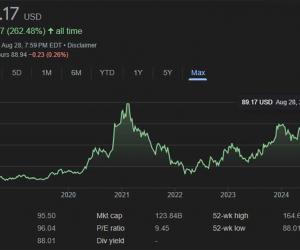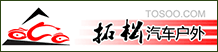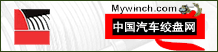论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
西方传统认识论在知识观上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命题偏见”( propositional bias),认为最重要的、最值得哲学关注的知识是命题性的knowing-that,知识是有真假的命题。
这种命题导向的对知识的理解,强调知识和命题表达之间具有内在关联,认为凡是知识都应该能够作语言的表达。 这种知识观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比如,在 柏拉图对话《拉凯斯篇》就可以看到这种知识观的雏形。 《拉凯斯篇》主题是“勇敢”。在对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我们既然知道,那么也一定能够说出来” 。作为将军的拉凯斯说:“我认为自己对勇敢的性质是知道的,但不知怎么地,我总是抓不住它,无法说出它的性质。” 按照苏格拉底的标准,拉凯斯既然不能说出勇敢的性质,那么实质上他不知道什么是勇敢。
“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说,不能说出来的就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个思想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伽利略的著名论断“自然之书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到莱布尼茨“普遍的语言”的构想,再到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知识观发展的清晰脉络。挪威哲学家约翰内森( K.S.Johannessen )指出,在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观的框架内,“知识和语言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知识应当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条件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有不能用语言来充分表达的知识的可能性,完全是不可理喻的。”
金岳霖对知识的理解,基本上也在命题导向的知识观的范围之内。他区分了元学的态度和知识论的态度,认为元学的本体非名言所能及,属于非名言世界;而知识经验则能用命题来把握,属于名言世界。他的知识论关注的是所谓平平常常的知识,“平平常常的知识所发生兴趣的总是名言世界,而名言世界是能以名言去区别的世界。”
二战以后兴起的默会知识论( theory of tacit knowing/knowledge )对西方哲学史上这种根深蒂固的知识观提出了挑战。默会知识这个概念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内涵,但从字面上看,它首先和知识的语言表达相关。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作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默会知识论挑战的是什么?
默会知识论的矛头所向,就是传统认识论在知识观上的命题偏见。有意思的是,哲学家们对他们所挑战的对象,各有不同的表述。比如,波兰尼把它刻画为“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赖尔称之为“理智主义的传奇”,欧克肖特把它概括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技术的至上性”的教条,从而展示了这一认识论进路的多重面相。
众所周知,默会知识这个术语首先是由波兰尼提出的。波兰尼提出默会知识论,就是要挑战 17 世纪科学革命以来所形成的“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 the wholly explicit knowledge )。默会知识论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论事实:“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不难看出,这一出发点和《拉凯斯》中的“凡是知道的就一定能言说”正相反对。
波兰尼自己曾举了不少实例来阐明“我们所知道的多于我们能够言说的”的事实。 在此,受欧克肖特的启发,笔者愿用一个中国哲学的例子来对这个命题作一番说明。
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庄子天道》)
关于斫轮,轮扁所能言说的是,“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所以要“不徐不疾”诸如此类的一般性的原则,这当然是他能够传达给他的儿子的,但是,他的儿子即使把这些一般性的原则记得烂熟于心,也还是不能斫轮。显然,轮扁关于斫轮所知道的多于这些抽象的、一般性的原则,那么,多的是什么呢,多的就是那种得心应手而口不能言的斫轮的技艺。
轮扁的那种得心应手而口不能言的斫轮的技艺,就属于波兰尼所说的默会知识的范畴。波兰尼说“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描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地图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 波兰尼把第一类知识称作明确知识( explicit knowledge ),把第二类知识称作默会知识。波兰尼所理解的默会知识,是指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所拥有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行动中的知识,或者说是构成行动或者内在于行动的知识。 17 世纪以来,在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知识,都是指用语言符号来表达的知识,由于默会知识不采取这种表达形式,所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其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在波兰尼看来,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是有关人类知识问题上的一种狭隘观点。
波兰尼关于默会知识和明确知识的这种划分,和赖尔关于 knowing-how 和 knowing-that 的区分十分接近。赖尔严格区分 knowing-how 和 knowing-that ,就旨在挑战认识论研究中的“理智主义的传奇”( intellectualist legend )。赖尔所说的 knowing-that 有各种类型,但都能够表述为命题。 Knowing-how 的知识与此不同,“当一个人知道如何做某种事情的时候(比如,开有趣的玩笑,指挥战争或者在葬礼上举止得体),他的知识就体现或实现在他所做的事情中。” 与 knowing-how 和 knowing-that 的区分相联系的一个重要区分是智力( intelligence )和理智( intellect )的区分。赖尔讨论了一系列的智力谓词或智力概念,如“智慧的”、“聪明的”、“精明的”、“狡猾的”、“有创造力的”等,以及与之相反的是“愚蠢的”、“傻呼呼的”、“迟钝的”、“不明智的”、“无创造力的”等,他认为,这些智力谓词都可以用 knowing-how 来加以定义。理智则属于 knowing-that 的范畴。“当我们谈到理智,更准确地说,探讨人的理智的各种机能和行为时,我们主要是指构成理论思维的那类特别的行动。这类活动的目标是关于真命题或事实的知识。” 赖尔指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明了 knowing-how 和 knowing-that 的区分,但是,“理智主义的传奇”则不是忽视 knowing-how ,就是试图把 knowing-how 归结为 knowing-that ,把智力归结为理智。
与波兰尼和赖尔相仿,欧克肖特区分了实践知识( practical knowledge )和技术知识( technical knowledge )。在此问题上,欧克肖特的目标是要质疑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关于技术的至上性的教条。欧克肖特认为,包括科学和艺术在内的人类活动都包含两种知识,即技术知识和实践知识。技术知识“可以被表述为规则、原则、指示和准则——总起来说,用命题来表述。” 而实践知识则不能作这样的表述,“它的正常表达是以一种习俗和传统的做事方式,或者,简而言之,是以实践的方式。” 但是,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则强调技术的至上性( the sovereignty of technique ) ,它不承认实践知识是知识,认为一切人类活动中所含有的唯一的知识要素是技术知识。
二、默会知识论正面肯定了什么?
与完全明确知识的理想、理智主义的传奇和理性主义的“技术至上性”的教条相联系,传统的认识论专注于明确知识、 knowing-that 或者技术知识的研究,而默会知识论则充分肯定了默会知识、 knowing-how 和实践知识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在传统认识论的论域之外,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但是,默会知识论所肯定的远甚于此,它还有更强的主张。它不仅肯定在明确知识之外还有默会知识,在 knowing-that 之外还有 knowing-how ,在技术知识之外还有实践知识,而且断言,默会知识之于明确知识, knowing-how 之于 knowing-that ,实践知识之于技术知识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和根源性。
波兰尼说:“默会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知识不是默会知识就是根植于默会知识。” 这段话,堪称对默会维度的根源性和优先性的典型表述。默会知识是明确知识的基础,一切明确知识都有其默会的根源。波兰尼认为,从根本上说,语言符号的使用本身是一种默会行动。具体来说,这种使用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环节,即对于语言符号的赋义( sense giving )和理解( sense reading )活动,缺乏这两个环节,明确知识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而这两个环节都是默会的。所以他的结论是,默会能力是人类获得和持有知识的终极机能( ultimate faculty )。
赖尔也认为 knowing-how 逻辑上先于 knowing-that 。无论是发现还是拥有一种 knowing-that 的知识,都以 knowing-how 为前提。“一个科学家首先是一个 knower-how, 其次才是一个 knower that 。除非他知道如何发现,他不会发现任何特定的真理。” 当某人在发现了一种 knowing-that 的知识以后,如果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就不能说他真正地拥有这种 knowing-that 的知识。“有效地拥有一种 knowledge that ,得知道——如被要求——如何来使用那种知识来解决其他的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 赖尔区分了对知识的“博物馆式的拥有” (museum possession) 和“工作坊式的拥有” (workshop possession) ,后者把知识的使用作为一个内在的环节包含在自身之内,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对知识的拥有。和 knowing-how 逻辑上先于 knowing-that 相应,智力相对于理智也是在先的。如上所述,在赖尔那里,理智主要是指一种理论活动,但是,赖尔指出,理论活动既可以充满智慧地展开,也可以以愚蠢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思索命题的活动体现了智力,预设了智力,以智力为前提条件。
和波兰尼、赖尔相仿,欧克肖特也断言实践知识先于技术知识。他说:“烹饪书不是一个独立的、烹饪可以由此产生的起点;它只是某人如何烹饪的知识的一个抽象:它是这活动的继子,而不是这活动的父亲。” 与此相类似,政治意识形态,作为一套抽象原则,“不是独立地预先策划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的规划,而是从人们惯常从事参加他们社会的安排的样式中抽象出来的观念体系。” 也就是说,先有政治活动,然后才有政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对政治活动的抽象、缩写。
三、默会知识论分析的范例( paradigm cases )是什么?
如上所述,赖尔认为,我们的理智的本质是理论活动,理论活动思索的对象是各类命题。“数学和各门已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是人类理智的典型成就。” 如果说,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人类理智的典范性的成就,属于明确知识的范畴,那么,默会知识的范例则是体现了智力的各种机能,如眼光( flair )、鉴别力 (connoisseurship) 、判断力、趣味、技巧、想象力、直觉和创造力等。智力逻辑地先于理智,明确知识的产生是我们运用上述机能的结果。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这些东西被当作主观的、心理的东西被放逐,而默会知识论认为,这些机能中隐藏着有关人类认识最激动人心的秘密。
四、默会知识能否传递?如果能够,那么如何传递?
让我们回到轮扁斫轮的故事。轮扁认为,斫轮的技艺“ 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 ”,这是对技艺本性的深刻体会,为默会知识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证。但是,笔者不同意轮扁的如下说法:斫轮的技艺, “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于臣 ”。 轮扁 认为技艺不能传递,未免把默会知识神秘化了。其实,默会知识一点也不神秘,它能够有效地在人际传递。当然,默会知识的传递方式和命题性知识不同。由于命题性知识能够编码化,所以能够通过书籍、课堂教学、函授等方式来传递,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远程教育等也是传递明确知识的有效途径。但是,象技巧、技艺、眼光、判断力、鉴别力等默会知识,就很难以这样的方式来传递。就默会知识的传递来说,笔者认为,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实例之于一般性的规则、准则的优先性。
在传递默会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当然能够从展示技巧、技艺或者眼光、判断力、鉴别力的活动中能提炼出一些一般性的规则、准则、规条。比如轮扁就提炼出了“不徐不疾”的斫轮原则,亚里斯多德也提出了“无过无不及”的道德生活的准则。这些一般性的规则、准则当然也有用,但是用处有限。赖尔说:“它们在教学法上是有用的,即在那些还在学习如何行动的人的课程中是有用的。它们属于新手的学习手册。……它们是蹒跚学步者的围栏,也就是说,它们属于方法论,而不属于有才智的实践的方法。” 技艺和鉴别力等远比这些抽象的一般性规则、准则要丰富,它们不能归结为这些一般性的规则、准则。因此,即使有人把这些一般性的规则、准则背得烂熟,他还是没有掌握技艺和拥有鉴别力。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掌握技巧、技艺,培养眼光、鉴别力、判断力、趣味等等?
一种重要的途径就是诉诸体现了技艺、判断力、鉴别力等的具体的实例,去感受、体验、移情,甚至去模仿这些典范性的例子。比如,要培养一个人的美学趣味,重要的不是去看什么“文章做法”之类的东西,而是要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去读经典作家的典范性作品。要提高一个人的道德行为能力,一般性的道德规范、道德戒律的作用常常是有限的,而道德楷模的人格事迹往往具有更强的道德感召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诚哉斯言!而榜样就是实例。就科学研究的能力的培养来说,范式( paradigm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库恩那里,范式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学科母体,即一个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价值、公式、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二是指这个整体中的一个成分,即共同体分享的范例( examplars ),它们是具体的谜题解答( concrete puzzle-solutions )。在范式的两种涵义中,库恩显然更重视第二种涵义。正统的观点是,“除非学生先学会理论及若干应用它的规则,否则他根本不会解题。科学知识蕴涵在理论和规则中。” 库恩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常规科学中,具体的谜题解答作为“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 在他看来,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的问题上,范例之于规则具有优先性,规则从根本上说导源于范例。
其次,师徒关系的重要性。乍看起来,在这个教育高度发达的时代来重提师徒制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真理并不会因为古老而不再是真理。在默会知识的传递问题上,师徒模式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波兰尼说:“一种难以说出其细节的技艺……它只能通过实例由师傅传递给徒弟。这就使其传播局限在亲身接触( personal contacts)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发现工匠的手艺总是在一个严格限制的地域性传统中延续。” 不仅工匠的手艺如此,科学研究的技艺也是如此,“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建立在一个地域性的传统之上,它包括了大量的直觉性的进路和情感性的价值,这些东西只有通过亲身合作(personal collaboration),才能在代际传递。” 就默会知识的传递而言,师徒之间的亲身接触、亲身合作十分关键,学生只有在和导师的亲身接触和合作中,通过内心的揣摩、联想、体会、移情等等,才能有效地从导师那里学到技艺、鉴别力等形式的默会知识。默会知识传递中的这种师徒间的亲身接触和合作,和远程教育的所谓遥远在场(telepresence)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上是从四个方面对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所作的一个初步论述。默会知识是一个极具生发性的概念,自其产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它在不同倾向的哲学家那里得到了响应。哲学家们从不同的哲学背景出发,探讨了与默会知识相关的种种问题,相互之间不断对话,形成了不同的研究传统,大致有现象学-诠释学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波兰尼传统,为认识论研究展开了一个新的理论境界。笔者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地介入到这场正在展开中的讨论之中,调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努力探索,推陈出新,作出我们的理论贡献。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参见,Barry Allen,“What was epistemology?”in Robert Brandom ed. Rorty and His Critics , Blackwell, 2000, pp.220—236.
参见,Kjell S. Jonhanessen, “Knowledge and its Modes of Articulation: A Sketch of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Our Tacit Hold on Reality”, in Uniped , Vol.22, No.3, 2000.
参见,Harald Grimen,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LOS Center (Norwegian Research Center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1991.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2002年,人民出版社,第182页。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2002年,人民出版社,第188页。
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学文集》,童世骏、郁振华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77页。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8页。
参见,Michael Polanyi: Tacit Dimension , Peter Smith, 1983.pp.4-8.
欧克肖特在一个注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但没有作太多的发挥。参见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9页。笔者很重视这个例子,希望从中读出更多的内容。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12.
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 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 1946, Vol.46, p.8.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商务印书馆, 1992年,第20页。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0页。译文参照英文版作了修正。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中译本把(the sovereignty of technique)译为“技术的霸权”,似乎可以商榷。
Michael Polanyi: Knowing and Being , Routeledge,1969, p.144.
参见,郁振华:《波兰尼的默会知识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8期。
Gilbert Rly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 Vol46, p.16.
Gilbert Rly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 Vol46, p.16.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43页。
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页。
Gilbert Rly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in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 Vol 46,p. 1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8页。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 Routledge,1958, p.53.
Michael Polanyi, The Logic of Libert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p.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