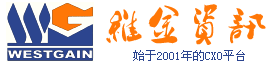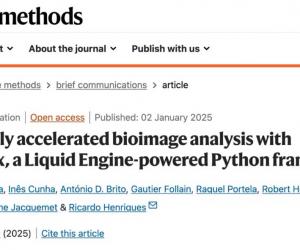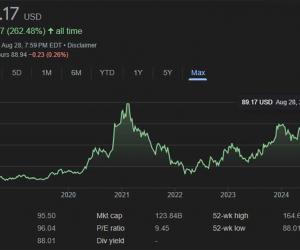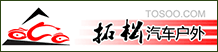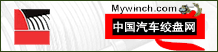未来从现在开始未来从现在开始:阿尔文·托夫勒
主持人(张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参与《对话》。今天的这个喧闹的世界充满着很多的变数,人们每天都面临着很多的困惑,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通往未来的路又在哪里?我想这个问题都在大家心头萦绕着。有一个人他的工作就是要为未来做打算,这个人在20多年前就曾经为我们画过一张通往未来的地图。在今天,这张地图里很多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他的名字跟《第三次浪潮》这本书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好,现在就让我们有请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先生入场,大家欢迎!我先想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特殊的嘉宾,坐在中间的这位女士是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副主任朱丽兰女士,大家欢迎!海迪.托夫勒,是托夫勒先生的夫人,也参与了他的许多著作的共同编著,大家欢迎!在她旁边的这位男士是中国网通公司的总裁田溯宁先生,这位先生是深圳科兴公司的总裁潘爱华先生。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在今天的这场节目里将一起寻找通往未来的这把钥匙。托夫勒先生,很多人都形容您是一个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人,您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您能够从很多在很多人看来毫无关系的一些社会现象中,把它进行有机的梳理,然后从中总结出现在的社会的动向和将来的一些走向。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我们很多人都感到有些困惑,我想把这些事件来跟您探讨一下,看看您对他们是怎么理解的,好不好?像恐怖主义事件的袭击,对《哈里.波特》的狂热,或者是经济的放缓,中国的崛起,这些事件它们彼此之间有没有联系?
托夫勒:我相信它们是彼此联系的,例如《哈里.波特》,就是一次成功的全球营销,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早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世贸组织也是和全球化相关的,各国经济跨越国界,彼此融合。现在发达国家工业模式本身已经解体,第三次浪潮的新模式正在出现,经济上的变革不可能不带来文化、宗教、家庭结构和政治的相应变革,所有这一切是一起变化的。第三次浪潮带来了多样性,包括文化、宗教和其它领域。
主持人:现在中国正在全面地走向世界,今天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我们申奥成功,足球进入世界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成功地在上海举行,那么中国现在又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系列的事件在您心目中意味着什么?
托夫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对世界也是有好处的,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非常注重出口,出口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其它亚洲国家通过出口快速发展,遵循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在70年代开始大量出口,所有国家应该更注重发展国内经济而不能够过分地依赖出口。
主持人:从今天正在发生的许多事件里面,我们从哪些事情能够看到一些未来的萌芽?
托夫勒: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再次告诉大家,没有人能够确定地预知未来,未来是没有确定性的。我们不使用预测这个词,因为预测暗示着某种确定性,我们可以预知未来的某些事情吗?答案是肯定的,全世界有600万未来学家,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未来学家。例如我可以肯定现场观众都可以预知节目结束后自己会干什么,他们可能会回家,可能会去吃饭,这也是一种预测,但这是短期预测。当我们开车时,我预测不会撞车,这也是一种预测。人们的生活中不可能没有预测,不同之处在于未来学家看得更远。就像你所说的不只看到一种变化,而且会对变化进行有机的梳理。例如现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正在开始有机的结合,近年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使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中的许多突破成为可能,而未来基因工程和生物科技中的突破会改变信息计算的方式。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嘉宾都对我们谈论的这些问题非常有研究。朱女士,我知道托夫勒先生的书您也都看过,您对它里面的许多观点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跟他一起来探讨,是吗?
朱女士:因为我以前是科技部部长,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科技本身是个双刃剑,它可以用于人类的造福、和平,也可以毁灭。而且有一句结论,你说了,可能用于这种情况下的话,人类也可能毁灭在自己的文明创造当中。因此我想对于这个双刃剑的问题,我想引用你的一个结论,引申一点,你这个结论我很同意。他说没有经济的未来,只有未来的经济。为什么?说经济的未来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而未来的经济是一种宽泛的观点。因为它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所以我想,将来的科技可能也不能叫科技的未来,要叫做未来的科技。
托夫勒:别人问我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总是回答他这取决于你在星期几提这个问题。多年来,别人感到悲观时,我们可能会感到乐观,反过来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不会进入高风险和不确定的时期,在我和海迪合著的《未来的战争》一书中,我们谈到了反对战争,我们谈到了和平,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维护和平的方式却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发动战争的人使用的科技手段,维护和平的人们却还没有发现。
主持人:田先生他曾经跟我说过在第一次看到《第三次浪潮》这本书,然后看到跟这本书同名的电视片的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心潮澎湃,可以这么说吗?
田溯宁:可以,我说我就想如果有一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的话,可能就是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托夫勒先生的《第三次浪潮》。我还记得非常清楚,1983年冬天,我那个时候在沈阳辽宁大学读书,下着雪,我开始读到从一个朋友给我寄来的一本书,从北京。读到的那本书不是这样的,是一种绿颜色的封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所以一晚上就读完这本书,我记得晚上也没有睡觉,那种激动的心情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
主持人:我们可以问一下,1983年的时候您是多大?
田先生:我1983年的时候21岁,在读生物系。
主持人:为什么那么激动?21岁的时候看到那本书。
田先生:我想跟这个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1983年的时候,整个经济改革的思潮刚刚到来已经开始听到各种各样的企业、经济这些词,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困惑,将来到底干什么?未来世界是什么样?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生物学家,生物学家将来能做什么?而且对外部世界又了解,又不了解。这时候读到托夫勒先生这本书,而且很快看到那个片子,我当时就感觉到找到一种未来。我觉得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两点,第一点,它特别清晰地把人类社会分成了三个部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未来的信息社会,而且用这个词,浪潮。第二个观念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他觉得在每一次工业革命变化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机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知道外部世界很好,连看到一个外国人觉得身上的香水味都很特殊,觉得外部世界特别好。我记得我收到我母亲到美国的一封信,跟我说美国真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觉得外部世界特别好,而且觉得中国跟人差距非常之大。但是读完这本书之后,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每一次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机会。所以他这本书很重要的观点在,美国由于抓住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很快从一个游牧国家,连第一次浪潮都不是,进入了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样他也谈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掌握第三次浪潮这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的浪潮,我们很快也能够赶上发达国家。我觉得这个震撼,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这种未来。而且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感受很深的话,他这本书,我想我们很多人,我现在一谈到,还记得这本书用非常优美的文学语言描述了一种既是未来又是现实,用这种诗情画意般的语言描述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我有一段话能记得,还有一些话记不住了,在来之前又翻了一下,我想即便我们今天读这段话还是能够有很多引起我们的心潮澎湃,我给大家读一读。它是在《第三次浪潮》的第一章开始的,它说1950年1月,20世纪下半叶刚刚揭下序幕,一个22岁的瘦弱青年人,带着新获得的大学文凭乘了一夜长途公共汽车来到他被认为现实的时代中心,身旁坐着他的女朋友,座位下放着一纸箱书籍。透过雨水冲刷的玻璃窗,美国中西部一望无尽的,连绵不断的工厂迎面掠过,这时灰蒙蒙的晨霭降临大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话我觉得非常的美好,特别向往。你想想在21岁的时候,读到一个22岁的年轻人,因为当谈到他为了寻找工业革命,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能当五年的工人,这种理想,这种激情和这种话,非常优美的语言,我觉得真是很难忘,我今天读它的时候还能够为他这段话感到激动。我想我们现在也是,我们正在一个信息化社会,中国正在一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大时代的面前,我觉得同样需要这种激情,需要这种探索精神,而对未来这种真挚的向往。另外一句话,就是你这本书最后的一句话,我想我一直还能背下来。他在这本书最后一句话说,就像革命的先辈一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我觉得这些话也是经常在很多情况下能够鼓励我,经常我想起来这句话,就感到对待未来、对待新兴的事物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主持人:您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不光是年轻人在做这些,包括当时朱丽兰女士,当时我们很多从事的事业已经蒸蒸日上正在发展的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看这本书,也在看这部电影,是这么回事吗?
朱女士:是的,我大概比你大多少,跟你妈妈一样吧。因为他妈妈我认识,我们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所以考虑的问题可能没有像年轻人的激情,可是更多的是探索。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所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走向如何,然后中国的本身发展肯定跟世界也是联系在一起,又会往前怎么发展,我觉得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思考。您说了,说技术是可以跨越的,教育是不能跨越的,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同时我更听到了你说需要把教育跟信息技术连在一起,同时也是您说的,你说教育从空间、时间和它的知识机构,和它的整个的模式要改革,这种作坊式的教育是不行的。那么怎么用信息化的技术来促进教育,实际上促进教育的本身是促进人的本身发展。最近我听了有一位先生,我想这位先生托夫勒先生可能认识,温世仁,他说他跟你已经有30年的交情,他称你是他的老师。认识吗?可能我那个发音你可能是另外一个发音了。
托夫勒:谁?
主持人:温世仁,温先生是中国台湾的一位未来学家。
托夫勒:是的,我认识温世仁先生。
朱女士:然后他最近提出了一个概念,我曾经跟他讨论过。他说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教育跟信息技术结合的话,他的一个命题是什么,叫网络连接梦想。那么怎么网络连接梦想呢?因为我们西部地区很贫穷,那儿的年轻人在处于一种封闭而且这么一种情况下,他没有看到希望。他说那儿的年轻人没有看到希望,那儿的老年人甚至连梦都不敢做。但是就是他到了那儿,在甘肃的一个旺羊川,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花50万块钱去建立了网站,去给他们送了计算机,一下就打开了他们的视野。现在就开始说这些人包括已经学习了的人,成为当地的人去传播这种信息的知识和观念。我想这样的做法就把第一浪潮、第二浪潮、第三浪潮,潮在一起了,这就是所谓的,您也说过三个浪潮可以多元化地发展。但是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通过信息技术本身把它连接起来促进它这种发展,那是可以一日千里地那么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又觉得发展中的国家要抓住这个机遇,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个信息技术,前途是光明的,在这点上我们可以说机会是均等的。所以我也曾经听见,有一个外国人说,说网络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所以就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很好地利用这个礼物,而且结合我们的情况来发挥创造,我认为前途的确是光明的。
主持人:技术可以推动我们教育的过程,能够加速这个教育的过程,我想这一点,田先生,这说到您心里去了。 田溯宁:从电信角度来讲,宽带电信产业是未来是很好的商业模式,这个没有问题。但宽带到底能给人们生活带来什么?尤其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像朱部长讲的,我们有七亿多人还在农村,所以说我们网通第一个在今年做的所谓我们公益性的项目,叫宽带希望小学。我们在宁夏选择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县城,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很多人可能现代文明都没有见过,第二次浪潮的汽车、火车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他们可能非常聪明,他们的智力可能跟比尔 盖茨,跟爱因斯坦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因为生错了地方。我们再想一想,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他能够在互联网上能跟北京景山学校的学生共同交流,通过互联网能够跟香港的一个学校进行交流,能看到卢浮宫,能看到世界上互联网上的很多的东西,他的生命会改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考虑 ,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不仅仅给企业带来利润,而且能改变生活。尤其能够通过提供这种宽带联接的网络,能改变中国农村孩子的生活。当然这个试验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每一年都能成为企业的一个公益型的项目。通过这个方面能够表明互联网如何能够帮助中国的农村学校,通过这样最新的技术实现您书上所谈到的新技术实现跨越,能够使整个的教育成本降低,使每个人能够有同样的机会,获得最优秀的教育。
主持人:潘先生,其实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两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了,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潘爱华:去年《时代》杂志在5月22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什么将取代技术经济》,它里面是非常肯定地说了一个结论,就是在21世纪的20年代,信息经济将让位于另外一个经济,这就是生物经济时代。所以这个文章里面也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一个观点,怎么样从采植经济,到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然后下一个阶段的生物经济。
主持人:首先我想问问托夫勒先生,同不同意他说的这句话?21世纪是生物科技的世纪。
托夫勒:在今后的25年中,我们会看到令人震惊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生物技术和相关领域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它许多领域中的突破它们还没有得到宣传,能源、光学和其它领域都有所突破,所以真正强大的技术,不是单一的一种技术,而是几种技术的融合。当多种技术融合在一起,冲击将会是爆炸性的,不同于单一领域中的有限冲击。今后很多领域的研究将以一种现在难以预测的,令人惊奇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生物技术可能会成为领头技术,但是还会有其它领域的科学发展,它们同生物技术相互作用。因为变化太快了,我们也不能肯定,我们只是猜测,也许在2050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生物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来临了。这听起来好像是科幻小说,但我们过去很多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一样的东西今天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主持人:咱们就拿潘先生和田先生来做一个例子,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到底会怎么样结合?
潘爱华:田先生已经自己就结合了,因为他原来是学生物学的。
朱女士:我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现在这个例子很多。你比如说现在的生物技术,你要离开了信息技术你没法活的,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你那儿的东西他又给你创造了,很好的一种应用的机会,很明显的。比如说生物芯片,对不对。Life On Chip,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芯片,他是专家,这是一个。还有,像生物信息学,把这两个领域都连在一起了。现在大量的生物的技术,DNA的计算机的出现等等。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不要强调生物经济一定要压迫信息经济,我是同意托夫勒先生的观点。我觉得现在是个大科学综合在一起,你只要说是压过,你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你那个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已经不是过去第二次浪潮的生物经济,而是说整个大的广泛的。因为人家最后说,将来的人,我告诉你也可能就是装配出来的,也是可以的,是这样的。你哪个器脏坏了都可以的,可以是生物体的,也可以是硅片的,也可以是钢铁的,什么都可以的。
潘爱华:刚才朱部长讲得非常对。因为生物技术它是依靠很多的技术来支撑和发展的,比如我们讲下一代计算机是什么呢?很多人预测肯定就是刚才朱部长讲的DNA计算机,它可能运转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假如人脑的研究有突破的话,将来计算机,也就是信息怎么样跟人脑结合在一块。甚至有些人预测说以后很多学习可以变换一种方式,就是弄个芯片植到脑子里去,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用学了。
主持人: 那太幸福了,那时候的孩子,你看样子是被朱丽兰女士给说服了,是这样吗?
潘爱华:是,因为朱部长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老师。
主持人:我想听一下田先生,当第一次听到他说2020年生物科技将取代信息科技成为经济主要支柱,您听到心里有没有一惊?或者是不相信,没那回事。
田溯宁:没有。我觉得因为我学了10年生物没有学好,好不容易转到信息化上来,我不能再转了。一定先把信息化,把宽带先做好,做到底,我想我这一点是坚信不移。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结合肯定是必然的,各种相互结合。但是这里我想可能有不同的层次,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未来20年,还能奋斗20年,或者二十几年,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做好,把宽带能够铺遍中国的千家万户,我觉得此生足矣。
主持人:所以要坚定地走下去。
田溯宁:坚定地走下去,然后至于跟生物各方面的应用,我想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应用。但是生物技术或者信息技术,宽带网的技术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生产、工作、娱乐,这个效应真正发挥出来可能还需要10年,或者20年的道路。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托夫勒先生在这个宽带的社会里,当我们有了一个高速连接以后,这将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和工作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托夫勒: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住在一座山的山脚下,山顶上有一个水库,水从山上流下来,我们的房前有一个水箱,每天早上都会来一辆卡车,有人从卡车里出来走到水箱前打开水箱检测水质是否纯净。美国每天有成千上万辆卡车做这项检测水质的工作,而我肯定这项检测水质的工作可以由感应设备来完成,而且有可能完成得更好沿着水流的方向放一些感应器,我们将会有智能水流系统,这些感应器可以互动。我们将会有智能型公路,智能型房屋,智能型服装,在我们周围有许多感应器,我们有可能都看不见,因为它们太小了,但它们可以互动。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像童话。明天的世界中这些事情也可能不会发生,但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我坚信它会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发生。我们今天铺设的宽带网未来有可能不够用,我们还需要铺更多的宽带网,制造一个智能环境,使环境更干净,生命更健康。
主持人:在您的另外一本书叫做《未来的冲击》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当制造业之后,服务业将成为经济的支柱,服务业之后,其实现在有一种新的名词叫做体验业将成为经济的支柱。也就是说,体验这个词,其实您在20多年前就已经从您的书里说出来了。
托夫勒:是的。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制造业经济之后我们将进入服务业经济,然后越来越多地经历体验经济,人们购买各种体验。看电影就是购买一种体验,滑雪也是一种体验,旅游也是一种体验。就像海迪说的,这不是未来发生的事情,而是现在就已经存在的。几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看见一幢蓝色的小房子,只有一层,既不现代也不特别,就像一个盒子一样,但外面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候。我问给我开车的年轻司机他们在排队等什么呢?原来他们在等着到房子里去参观冰雪,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冰雪,他们的国家很炎热,他们想要体验冰雪的感觉。我们都想要体验,没有体验过的感觉,人们会创造越来越多的跟体验有关的经济活动。
主持人:说到体验业,我知道姜奇平先生对此应该是非常有研究,而且最近一直在围绕这个词在做很多深刻的思考,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姜奇平:我觉得随着宽带的发展,我觉得给人们生活最大的一个改变,我的判断会是那种以假乱真的体验,会真的成为一种现实。因为在过去在窄带拨号上网那个时候,你想传一个照片,你的心情都没有了,然后那个照片才下来,对吧。你有这种经验吗?真的,本来看着想激动,但是到那个照片下来已经不激动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家里就是宽带,拿着几个笔记本同时用宽带上网,这个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字,爽,感觉特别的爽。这是我们衡量体验业的一个标准吗?爽字,我觉得是。当然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讲,我认为马斯洛当时说的高峰体验,这个就是它的学名。过去我们说产品经济里面,说什么东西是控制标准,就是质量和价格,那到了这种体验经济里,什么体验好,什么体验不好,质量怎么控制,就看它到底爽不爽,酷不酷。所以我们到了最好,就是酷毙了、 帅呆了,对吧。这就是说它的质量标准很高了,所以现在我认为,在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什么呢?它把酷毙了、帅呆了当做一个产业来开发,未来的这种体验,在未来的体验之中,是大家一起的这种体验。比如说像踢足球,大家一起上街狂欢的这种体验,会成为一种趋势。还是说自己在家卡拉OK,自娱自乐这种体验会占上风。
主持人:您是哪种体验占上风?
姜奇平:我觉得两种好像都可能。
主持人:我们听听托夫勒先生怎么说。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中,有一个复杂的词,叫做非群体化。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当我们从农场转移到工厂,社会的基础是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配送和大规模消费,大众教育和大众传媒一切都是大规模的,人们认为个体之间应该是相似的,工业经济处处强调同一性。当我们进入未来第三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我们不再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个性。生产开始以客户为导向,先进的工厂不再大量生产同一种产品,而是针对客户的需要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成本很低。因为运用了智能化的生产技术,不仅使有形产品可以个性化,体验也可以个性化。我们不再去看同一部电影,即使是同一部电影,但部分内容也会因人而异。情节可能会有点不同,电影中的角色可能会由不同的演员扮演,或者是你自己可以参与其中。我们正在脱离群体化体验,转向个性化体验,越强调个性,你越会在社会中感到孤独。这是我们为了更多的个性而付出的代价,所以你问我的态度是悲观还是乐观,我和夫人觉得就像又苦又甜的巧克力,这就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您在《第三次浪潮》这本书里也说过,社会中有很多守望者,像艺术家、作家、媒体工作者,在我旁边这位秦朔先生,他是我们中国一本非常有名的杂志,叫《南风窗》杂志的总编,你也应该算社会的守望者。
秦朔:守望者之一。我今天很高兴见到托夫勒先生,我读到《第三次浪潮》的时候当时我只有15岁,在读初三。当时我妈妈在一个工厂的宣传科,她有一天把这个书拿到家里,那是我第一次读到,但是对我那个时候的冲击可能没有田总那么大。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难忘的。我那个时候比较难忘的是什么呢?确实是像一个西方人讲的,像一把劈开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今天在这里我想跟托夫勒先生请教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了非常多前沿的问题,无论信息经济、生物经济,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国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叫做混合经济。就是又有那种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又有工业经济,又有信息经济。而且托夫勒先生也经常讲,技术不仅简单是技术,它还意味着跟技术相呼应的游戏的规则,商业的文化、人的思维方法、人的教育水准,那么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年代,要高度浓缩这段里程。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不仅是机遇,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中国有些企业家讲,说现在想赶潮,想弄潮,想往前奔,感觉不往前奔,坐在这儿是等死。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说,奔得太快,有的时候踩不到点,找不到市场,找死。还有一些说,中国的企业又要学洋枪洋炮,又要学土法上马,这些东西都很多。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在美国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因为高度的创新,他们获得了超额的利润。但在中国有很多的产业里面,最早的技术的创新者往往都成了行业里的先烈,最后都不是利润的分享者。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比如说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转型的过程中,怎么样去把握这个度,踩住这个点?
托夫勒:我认为没有能够踩准点的灵丹妙药。我们不仅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经济,而且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体系。以前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像一个探险家正在进入一种复杂的环境。几千年前的勇士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身处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的环境要复杂得多,所以没有一条放之四海皆准的道路。在海迪制作的电视片《第三次浪潮》中,有这样的台词,我们都在同一起点上,都是新兴文明的弄潮儿,都还摸不着道。
钟先生:托夫勒先生闻名于世,当然有很多著作,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第三次浪潮》。我们今天大家都讨论这个题目,我相信托夫勒先生把《第三次浪潮》看作是现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您认为第三次浪潮会经历多少时间?所以要不要现在就去考虑,什么是第四次浪潮?
托夫勒: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恒,第三次浪潮也不会永远存在。我和夫人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意见也不统一,我和夫人意见相左了50年。
海迪: 50多年。
托夫勒:这些分歧对我们的学术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人们会问第四次浪潮是什么样的?我的回答是生物科技,和由生物技术推动的浪潮。我的夫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她觉得情况不是这样。
主持人:让我们听听您太太的意见。
海迪:我认为生物科技的革命仍然是第三次浪潮的一部分,而不是第四次浪潮。
主持人:您认为第四次浪潮是什么?
托夫人:太空技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太空技术上投入很大,我们可能会离开地球。人类是独一无二的,我希望在别的星球上还能延续。我们还可以从太空中学到关于地球生命的很多东西,比如怎样保护地球生命等,这才是第四次浪潮。
主持人:我看到我们网上有一个观众,他就想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在您的著作里看到有关对中国的比较详尽的描写,是不是您有这个计划能够多关注一下?
托夫勒:原因之一是我们欣赏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有限,而更关注我们了解的东西。这并不说明中国不重要,而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中国的无知。
主持人:在你听完了今天我们在座的嘉宾和托夫勒先生,这一番有关未来的谈话之后,在你的心目中,未来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来很快地说一下,哪位观众愿意举手向我示意一下?
观众:我想还是这样讲吧,我非常感谢《对话》栏目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一个精神家园,讨论第三次浪潮,甚至第四次浪潮。人要生活在希望当中,总是看到前头,有非常美好的东西等人类去追求。
观众:听了托夫勒先生这个发言,虽然我现在目前心里还有很多疑问对未来,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未来是可以持续思考的,这是大未来。但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观众:未来就像姿三四郎,他的师傅跟他说的那句话,悟性在你的脚下。我觉得未来也是在你的脚下,需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主持人:好,谢谢。我也想听一下我们在座的几位嘉宾,潘先生,未来是什么?
潘爱华:在我的心目中,希望未来是生物经济,但是给我的答案是不知道。
主持人:田先生?
田溯宁:我相信我们的未来是无限宽广的世界。
主持人:三句话不离老本行。朱丽兰女士,未来是什么,在您心目中?
朱女士:我觉得未来寄托于我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和发扬。
主持人: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托夫勒夫人 ,未来在你心目中是什么?
海迪:我跟丈夫都认为,通向未来的轨迹不是直线,它会充满起伏,不会一帆风顺,途中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主持人: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请托夫勒先生来选择一种颜色,如果要你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您心目中的未来,这个颜色是什么?为什么?
托夫勒:我会选择蓝色。
主持人:为什么?
托夫勒:因为蓝色有不同的色调,英文中蓝色还象征着悲伤和忧郁,但这不是我喜欢的蓝色。
主持人:你喜欢的蓝色是什么样的呢?
托夫勒:我喜欢天空的蔚蓝,它象征着很多积极的事情。我们说拥抱蓝天,我们可以创造未来,我们不是被动的,我们要用行动创造未来。蓝色天空象征着激情,此外它也象征着太空,充分了诗情画意,所以我会选择蓝色来代表未来。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为我们描绘了这么美好的一个蓝色的未来。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的参与,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