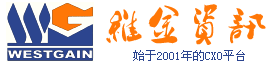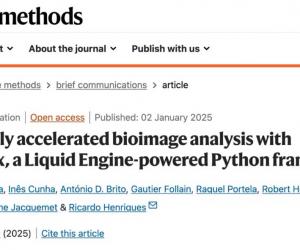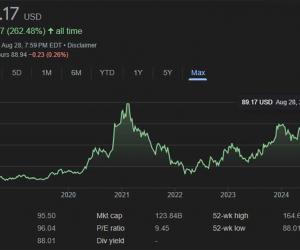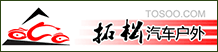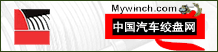如果城镇化“冷”下来了,会给经济带来什么?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很快,中国的城市研究也发展非常快。最近我看到一个电视新闻,主持人让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德曼推荐书给大家看,他推荐的叫《城市的胜利》,这本书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城市这个东西是人类有史以来发明的最好的东西之一,它的核心在于城市实现了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最密集使用和最有效配置,从而获得了最好、最经济的产出。因此,这样一个平台、一个载体,是最好的发明,最终将获得胜利。所以,城市永远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题。
但是,迄今为止,我认为中国的城市还没有胜出。虽然过去30年,我们的城市化速度是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快的,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增长速度。但是,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们的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人均GDP的水平,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滞后,首先是指54%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
城市是为了什么?城市不仅是要素的汇集,更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和人力资本培养环境的改善。因此,我们更要看在城市中有参与感,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均等的经济机会的人的比重。中国正好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指标,叫做“户籍城镇人口的比重”,到目前为止大概还只有37%。因此,按照37%的城镇化率来比较,我们的人口城镇化已经非常滞后了,和我们的发展阶段也不相符。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城镇。
因此,我想谈两个观点,我们的城镇化如何从内涵和外延两个角度向更深的层次推进。
首先,相对于城镇化来说,我们现在遇到两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于城镇化速度减慢,虽然我没有看统计数据,但是我肯定未来会真减慢。城镇化速度的放慢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是互为因果的。看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去曾经把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做过分解,经济增长第一来自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这些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在提高。从过去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的贡献,这部分是生产要素集中的表现,看上去改革开放从资本富裕的地方流向稀缺的地方,其实不是这样,反过来,都是从穷的地方流向富的地方。对中国来说,资本也好,劳动力也好,土地也好,所有的重要的生产要素都是向城市集中的。因此,资本的贡献,劳动力的贡献,土地的贡献,还有资源配置的贡献,就是我们的劳动力从富裕的农业,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本身,构成了我们整个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城镇化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做模型,完全会做一个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反过来,经济增长也会影响城镇化。当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对生产要素的吸纳、吸引力、汇聚各种优质生产要素的吸引能力也就会减弱,所以城镇化也会放慢,互为因果,构成中国经济的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做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我们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城市转移的过程,但这句话只是学究性的话,真实的现象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因为务农的那些人都是年龄偏大的,绝大部分是40岁、50岁以上的,他们不再转移。我们讲转移的时候,其实是指农村新毕业的中学生,他们毕业之后选择进城,而不是务农。本来我们假设他应该务农,结果他没务农,所以我们说他是农业转移劳动力。因此,真正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是16岁到19岁的人口。
我们最近看了一下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发现在2014年农村16岁到19岁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总量达到峰值,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这部分人口数量会负增长,并永远负增长下去。如果把年龄人口的图画出来,2014年到达峰值以后,是一个倒“U”字型的曲线,它和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相关。因此,把外出农民工的图也画上去,前些年两个图形是重合的,是一样的。自然你就可以判断,是不是未来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是负增长了。我们觉得外出农民工很有可能会负增长。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看到的就是负增长。第二季度虽有所恢复,但是整个前半年是0.1%的增长率,而去年还是1.3%,2010年之前是每年4%的增长率。因此,外出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减慢,也是城镇化减慢的一个原因,这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生产率未来的提高速度可以假设,“十二五”时期,我们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到7.6%;明年开始进入“十三五”,假设改革效应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其他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能只有6.2%。
我们不希望只有6.2%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我们在探索改革的红利。改革红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蕴含了诸多的改革内容。但是城镇化也减速了,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它?我觉得城镇化面临着一个挑战。前一个挑战是减速;第二个挑战是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城市的管理能力和资源的配置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能力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或者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也就是说,一是城镇化本身速度将会减慢;二是城镇化与经济互为因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将导致城镇化速度减慢,构成中国经济新的挑战。
虽然我们受到资源的约束,但是人力资本是可以改善这些约束的。最简单的一条,北京缺水缺到这个程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用空气一样在使用自来水,自来水价格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于没有,这就是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造成的。所以,在这个发展阶段,你不要指望它有这么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城市管理能力。因此,就必然出现“城市病”、污染、PM2.5,环境变成1000名以外的,交通堵塞,以住房为主的生活费用大幅度的飙升,飙升的结果不是我们抱怨,更重要的是它降低了优质资源向这儿集中的吸引力。好的人才可能还是来,但是来了以后,是不是把真正的人力资源用在创意性的活动中?例如,应该踏踏实实做学问、做智库的人,因为生活逼迫,不得已用更多的资源去挣外快,我想这些都是城镇化的一个表现。
因此,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能力不足,城市的边际报酬就开始递减了,资源配置就没有那么高了。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推进城镇化,否则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低。但是反过来,我们城镇化的边际报酬已经递减了,该怎么办?对于这对矛盾,我觉得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内涵的,就是我们回过头来不再看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我们看户籍人口的百分比。也就是说,如果把现有已经在城市常住的农民工和家属变成户籍人口,我们将会获得的人口红利的延续和新的潜在增长力的增长。因此,我认为这是立竿见影的人口红利。
另一个就是外延上的城镇化的道路,即区域性的一体化发展,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也就是说,北京可能有CBD、金融街,但是没有滑雪场,没有崇礼的环境;它有金山银山,可能没有绿水青山。因此,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会赋予我们一些新的重新配置的机会。而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部分,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占比接近一半。因此,未来我们生产率要提高,更靠这个资源重新配置。所以,差异越大,我们重新配置的机会也就越多。